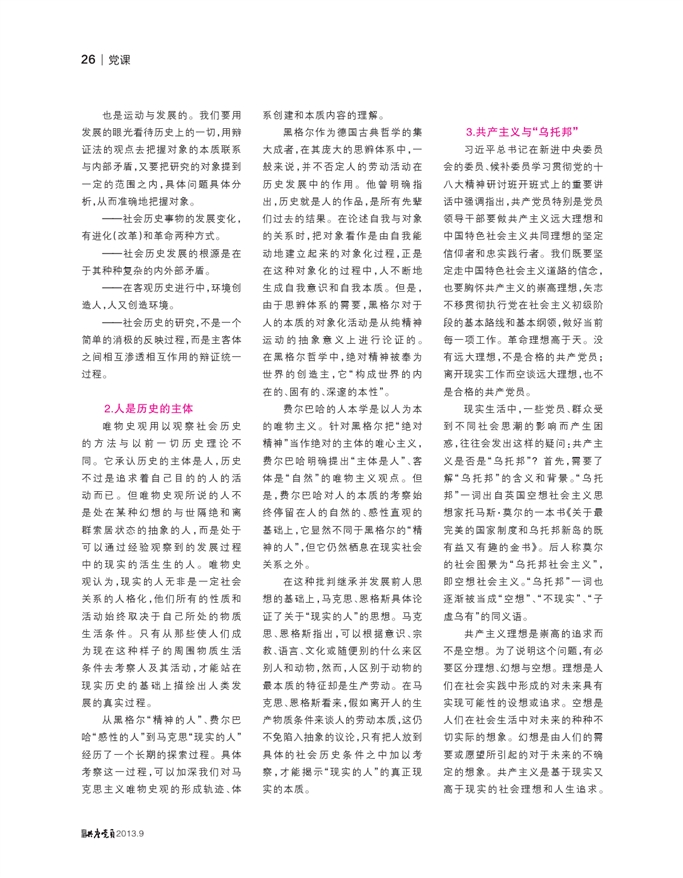群众路线:唯物史观是基石
也是运动与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一切,用辩证法的观点去把握对象的本质联系与内部矛盾,又要把研究的对象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准确地把握对象。 ——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改革)和革命两种方式。 ——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是在于其种种复杂的内外部矛盾。 ——在客观历史进行中,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 ——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过程。
2.人是历史的主体
唯物史观用以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承认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唯物史观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所有的性质和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物质生活条件去考察人及其活动,才能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
从黑格尔“精神的人”、费尔巴哈“感性的人”到马克思“现实的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具体考察这一过程,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轨迹、体系创建和本质内容的理解。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在其庞大的思辨体系中,一般来说,并不否定人的劳动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历史就是人的作品,是所有先辈们过去的结果。在论述自我与对象的关系时,把对象看作是由自我能动地建立起来的对象化过程,正是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人不断地生成自我意识和自我本质。但是,由于思辨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对于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是从纯精神运动的抽象意义上进行论证的。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被奉为世界的创造主,它“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针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当作绝对的主体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明确提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考察始终停留在人的自然的、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它显然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的人”,但它仍然栖息在现实社会关系之外。
在这种批判继承并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论证了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语言、文化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然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却是生产劳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假如离开人的生产物质条件来谈人的劳动本质,这仍不免陷入抽象的议论,只有把人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加以考察,才能揭示“现实的人”的真正现实的本质。
3.共产主义与“乌托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群众受到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产生困惑,往往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首先,需要了解“乌托邦”的含义和背景。“乌托邦”一词出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一本书《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后人称莫尔的社会图景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一词也逐渐被当成“空想”、“不现实”、“子虚乌有”的同义语。
共产主义理想是崇高的追求而不是空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区分理想、幻想与空想。理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未来具有实现可能性的设想或追求。空想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未来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幻想是由人们的需要或愿望所引起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的想象。共产主义是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